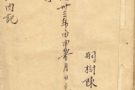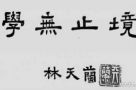重阳拜访高时良先生
刘思衡 2009/12/4 15:27:25 19696点 永安之窗高先生在福建师范大学从教三十余年,早已退休在家。我托师大的一位朋友先向高老通报,以便前去拜访。朋友说他与高教授未曾谋面过,但高教授在90岁高龄时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,轰动了师大的师生,很多原本不认识他的人也都认识了,至少也知道师大有一位耄耋老人参加共产党。这位前辈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,令我肃然起敬,更想尽早与他见面。于是,在重阳节的前两天我造访高老。高先生住在福州仓山阳光小区公寓里,当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,他十分高兴,大有半个老乡的意思,对我的来访表示欢迎。高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,口齿清楚,思维敏捷,除左耳听力差一点外,真不像是97岁高龄的人。我想初次见面,不敢造次,只是问了一些通常的问题,点到为止。其实,高老精神蛮好,也没什么顾忌,爽朗地谈了许多在永安的往事。当他讲到永安各界,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抗战激情,神情显得特别兴奋,也显得有些自豪。永安是抗战文化在东南半壁的一个重要据点,当时他在教育厅除编辑工作外,还做剧运工作和学生工作,青年学生高唱抗日歌曲、上演抗日话剧的热烈情景记忆犹新。跟他同事的一些共产党员、进步青年,尤其是卢茅居、陈培光等人,克服重重困难,夜以继日地工作,对他帮助很大,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新思想,也学会利用手中的笔,去跟敌人战斗。说到对永安的印象,高老说永安是个美丽的山城,人杰地灵,民众很朴实,青年人学习勤奋,抗日热情高涨,并说当时永安居住条件虽然差些,但物价便宜,生活不错。不过有一年发生严重粮荒,民怨极深 ,陈嘉庚先生还将陈仪省长告了一状------。
高老说,在师大工作期间,除担任教学工作外,还带硕士研究生,从事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,写了不少有关教育学方面的文章,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他发表了许多论文,出版了多部专著,如《学记评注》、《中国教育史纲》、《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、《中国教育家评传》、《中国教会学校史》、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、《中国师范教育通览》、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》、《学记研究》、《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》等等。其中《学记研究》和《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》分别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。我想这些成果得来不易,是高老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的结果,尤其是《学记研究》,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,是历代《学记》研究的集成之作,也是体现高老学术思想、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的一部力作。如今高老虽然年事已高,仍“退而不休”,坚持著书立说。今年3月,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《中国教育史论丛》,这是97岁的老先生给读者们的又一个奉献。目前高老手头还有一本《中国教育史史料学》尚未完稿,他说要写完这本书,才能歇笔!高老这种不老的心态和笔耕不辍的精神真令人敬佩!
我跟高老谈了许久,怕影响他休息,便起身告辞。临行前,高老还自豪地说到他的子女都在学校工作,也算是教育世家了。我抬头看到墙上省教委授予的“优秀教育世家”的匾额,感到十分羡慕。我冒昧地问高老有什么书可以送我一本作个纪念,他说手头没有了,却转身去拿了一份两页纸的打印稿“我走过的人生道路”给我,还很客气地说这些文字很肤浅,请指正。我心里想,甭说指正了,我要跟还跟不上呢!我匆匆看了一遍,文中除简要叙述个人经历外,着重讲了做人的道理,概括起来有这么三层意思:要有坚定政治方向,跟共产党走,不迷失方向;要关心国内外大事,了解形势发展,与时俱进;做学问要有毅力,锲而不舍,百折不挠,还要虚心求教师长同仁,不断扩展知识面。他还说,人老了总是要退休的,但退休后也不是无事可做,可量力而行做些研究工作,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”,再发挥一些余热。高老这些肺腑之言,寓意深刻,很有启发教育作用,值得我们好好领悟,仔细品味。
在回家的路上,一个满腹文章的耄耋老人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一个老知识分子,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、新中国建设、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,一路走来,在近一个世纪历史车轮的颠簸中,坚持教书育人,坚持学术研究,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史学家,并在他耄耋之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获得“教育先进工作者”和“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”荣誉,在95岁高龄获得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,实属不易,感人至深。我想,人总是要老的,退休的老人的确是该休息了,享受天伦之乐。诚然,如果健康状况许可,能够劳逸结合,发挥专长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象高老那样,为教育事业继续发挥余热,也是老年人一种很好的选择。让我们为高时良老先生健康长寿祝福吧!
作者工作单位:福建农林大学
林洪通编著: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
林洪通 3年前 8422点
林洪通编著: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的永安抗战文化,其中有邹韬奋
林洪通 3年前 7926点
林洪通编著:抗战省会永安,“永安大狱”中年龄最小的囚徒陈耀民
林洪通 3年前 13697点
林洪通编著:贺“永安大狱”被捕者谌震先生90寿辰
林洪通 3年前 8170点
林洪通编著:抗战永安出版界,聆听过斯大林报告的中共党员谢丹在战斗
林洪通 3年前 8677点

闽师之源 抗战学堂
8年前 30367点
毛主席鲜为人知的抗战佳句
安安 9年前 10983点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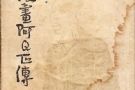
永安抗战珍品图书《漫画阿Q正传》
安安 9年前 10821点

陈主席战时手令辑要
安安 9年前 12511点
抗战旧址群项目获中央预算内投资4000万元
9年前 10329点